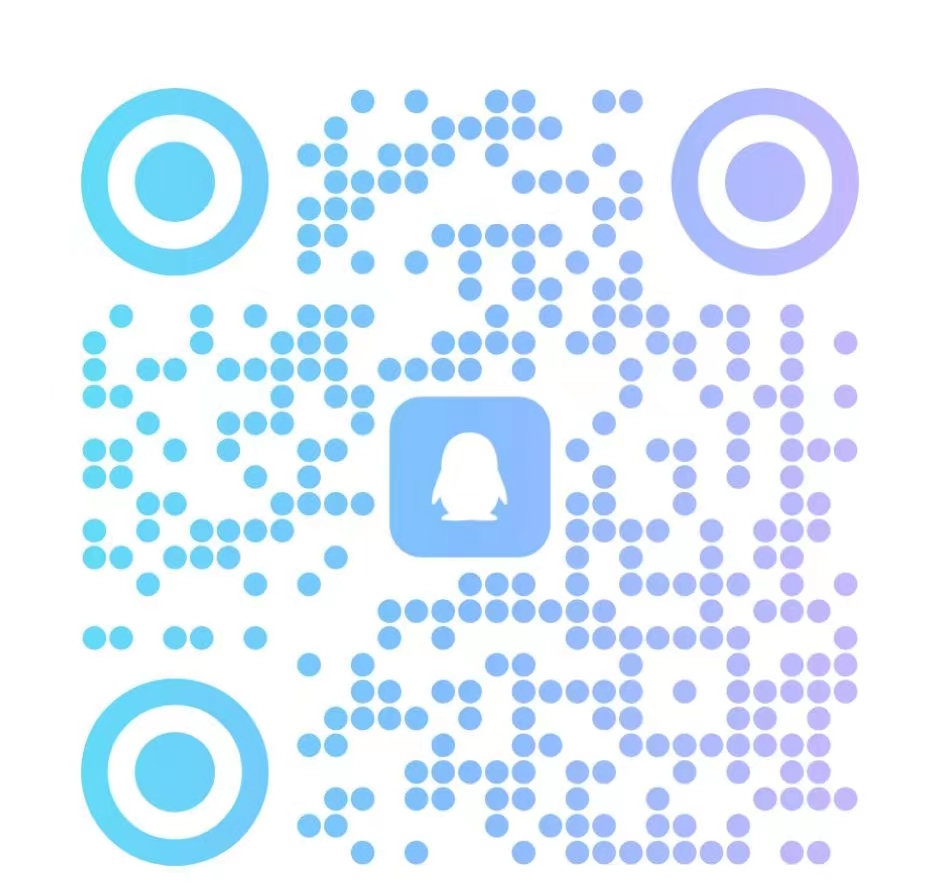天阴沉沉的,一丝风也没有,空气中夹带着些许腥气,太阳的余热还在起着作用,一条老狗呆呆地趴在村子口,尾巴有一搭没一搭地摆着,不远处浮着一座老桥,桥下有条河,前些年淹死过人,如今河边漫滩上长满了苇草,水面上浮着一层密密的蝇蚊。一阵风掠过,把雨吹来了。
起初是细密的小雨,如长长的银针,到了午夜,就成滂沱大雨了,还伴有轰轰的雷鸣,惊醒了梦中人,顷刻,一点点黑伞挤满了桥的一边,桥的另一边只有一把红伞,格外刺眼。熙熙攘攘之中有人大喊:“雨势太大,洪水冲垮了桥。”众人只见水里除了一节桥身还有一些家禽,有的在水里翻腾几下,就死了。
天太黑了。河里传来老牛的闷哞声,有一小队人扔掉伞跑回家去,拿着油腻腻的绳子,女人拿着手电筒照着,明晃晃的。只见那领队人将绳子摸出一端,再用手沿绳子端向后捋一节,停住打一个活结,再在绳端打个死结,套到活结里,然后瞅准一只在河里扑腾的羊,抛出绳子,一下子套住,再使劲拉,可惜绳子太滑,拉到半截羊便在水里不见了。那人又去捞别的活物,试了几次行不通,就蔫下来了,狠狠地拍打着自己的头,在手电的微光下,那脱光了头发的脑袋也明晃晃的。众人不再看他,只专心看河。
“孙大娘,那不是你家的老牛吗?”只听见一老妇啜啜泣泣,不说话。接着又有赵二家的驴,张三家的猪被洪水吞噬。好一阵哭喊声嚷成一片,说闲话看热闹的旁人一下子愣住了,下意识地伸长了脖子,瞪大眼睛,恨不得辨出在洪水里淹死的是不是他家的牲口。黑色的伞逐渐呈一字形长线般在桥的一边展开,没有发出一丁点儿点声音。
“哈哈哈——”很不合时宜发出的笑,桥的另一边,撑红伞的人。
这边人群的怒气瞬间被点燃,“傻子,你笑什么!你懂什么!你是不是被雨打瞎了眼?看看是不是也有你养的畜生!”
傻子被吓住了,但接着笑得更加厉害了。他到底在笑什么,他毕竟没有养牲口啊。
“傻子,真是傻,连打的红伞都是破的。”
“管他做甚,想想想自己吧。”
“只希望老天显灵,让我家度过一劫。”
雨渐渐小了,河上只剩下一残桥,一红伞,亮闪闪的,人不见去处。
雨停了,天边刚泛上一层鱼肚白,人群又聚上了岸边,洪水退去了,河面恢复平静,縠纹平整。只是在河边平滩上还残存着洪水留下的痕迹,苇草都倒了,不见什么别的活物,每个人都愣愣地杵着,瞳孔缩小,颜色如同秋天的残叶。
日头升到半空了,人群渐渐散去了。
有人路过孙大娘家的门口,看见一把红色的破伞,心下捉摸着,傻子保不齐在孙大娘家做坏事。连忙叫上一伙人拿着棍子冲进院门,只见傻子披着斗篷,上面还挂着几根苇草,斗篷上全是补丁,但修补得很整齐。傻子正用绳子将一条死牛的角缠住,拉到院子中心,头上密密麻麻的汗珠,流在脸上,傻子抬起头,乐呵呵地笑着。
孙大娘颤颤巍巍地走进来,又是一把老泪。人群中有人站出来说话了“傻子,你真傻,你是故意气大娘的吧!”
“傻子,你咋把孙大娘家的死牛拉上来了,有啥用呢,死都死了。”
“赵汉,你咋成这样了,前些年你还为咱村做过大好事啊,你把几个娃娃从洪水里救出来,那可是件惊动县城的大好事啊,可你看看你现在,洪水里捞死牛,有啥用啊,没用!”原来傻子叫赵汉,傻子有名,有姓。
“傻子,你——拉这死牛——作甚,你——哎。”孙大娘断断续续说道。
“傻子,傻子。”有个稚嫩的童声,接着是一阵哄笑。
傻子没有笑,傻子哭了,但流出来的只有几颗泪珠。
傻子走了,是低着头走出去的,带走了红伞。
傍晚时分,众人在孙大娘家里吃了顿牛肉面。
日子就这样平平的过去了,自傻子走后,村里没人见过他,也没人再提起他。乘凉的大树下,闲妇们在商量着该买几只猪崽,几头幼牛,谁都不记得曾经来过一次洪水。
天上有几只燕子掠过,山的一头有一层黑黑的云,山这头的村子上空太阳正懒洋洋地挂着,一闲妇道:“天气真好,一会就上集市看看。”
在河边的漫滩上,傻子枕着红伞呆呆地看着天空,他从山的这头看到那头,看见那层黑云了,心下一紧“要来洪水了”。可他没在笑,只是站起来拿上红伞,走向一户人家。
这天半夜,洪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