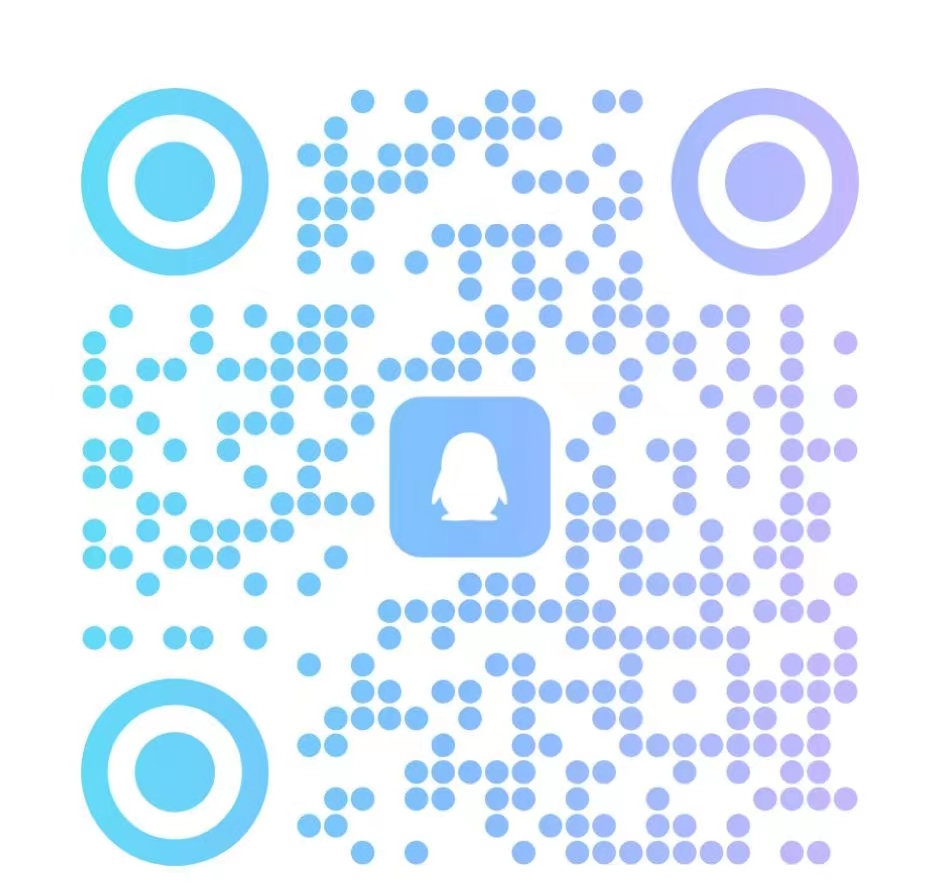何时将那柳条做了温床,编织虚幻的想象,虬壮的枝干又何时被沧桑刻满皱纹,何时太阳悄无声息从指缝间流走,又是何时,唯恐双溪舴艋舟。
闭上双眼,心头的那棵树,长满了璀璨的星子,大大的树洞里,藏匿着水晶的鞋子,精致的洋娃娃,转动的音乐盒,一切都是那么清晰,却又可望而不可及。倏然一切都远了,黑压压的笼罩着深不见底的乌云,父母的争吵声召唤出电闪雷鸣,我的树,精致呵护的树啊,忽然就老去了,黄叶萧萧,又变作了光秃秃的光景。漫长的冬天来了。
我的童年,是用空酒瓶砌成的堡垒,你能透过空明的玻璃望见苦苦挣扎的蝼蚁,但你不可触摸,你只能袖手旁观,因为你一触,它就支离破碎,会伤害到你,也会伤害到我。当我看到,一双向我伸出援助的手变老变丑,我知道,应该去缄默,不争不抢,这样,最安全。
我的老树依旧会藏匿东西,多半是破损的书籍,干瘪的树枝或是奇特的怪石,清一色的冷,我藉以此以毒攻毒,做个冷漠的人罢了。
年岁久了,所有的争吵声已经磨得耳朵长出了老茧,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一切都与我无关了,我的世界充满单双双行线,黑的白的,不计其数。我默默地走着,很早便开始想象我这一生,也姑且这样度过。
白驹过隙,我踏入高中的大门,满怀着远离深渊的希冀,默默穿行,直到遇到我的挚友,我们心中都住着那样一棵树,再没有明亮的星子,再没有昂贵的舞鞋,有的是植物的标本,泛旧的红橙黄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我们,在茫茫的雪原,固执的拥抱等待日出,可是,日出了,雪就会融化啊,会多一些冷意。所有的风平浪静下波暗涛涌。终于,一个夜晚,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夜深树高,风凉,泪水忍不住往下流。如履薄冰,如坠深渊,彻夜未眠。“信任与关心是否都是虚伪”无数次将我撕裂。我开始反思,为什么这种消极总是纠缠着我。
姐姐的一席话,醍醐灌顶,我恍然大悟。
生活的色调到底有多少?我拥有的又有多少?
思绪纷飞,骑在爸爸背上玩耍的我,超市小手握爸爸大手的我,跟发小互扔泥巴堆雪人的我,与同学爬山摘桃花的我,看春晚从凳子上掉下来哈哈大笑的我,拿到哥哥送的手表窃喜的我……一帧一帧地放大,将我带回那个被隆冬埋藏的记忆中。一瞬间,积雪融化了,我的树抽出了嫩芽,遍地的向日葵,一轮硕大的红日,满天的红霞。
生活的色调本该是明快夹杂着沉重,这是生命的常态,可倘若一叶障目,断章取义,便会走向极端,或是大言哄哄的不可一世或是敏感多疑的神经兮兮。
那时,我告诉自己,要本真的活着,不要被所谓的自我囚禁压抑。常青的春色,一点一滴地渗透到我的生命里。
与挚友真诚地交流,原来的信任与关系从未逝去,从不虚伪,曾经的我以为并非真实。我们和好如初,直到现在都是彼此生命中珍贵的礼物。我渐渐学会了接纳与信任,她的自律专注无不激励我鞭策我,慢慢变大变强,所有的失之交臂都是绝地求生的机会,我常常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和火红的枫叶。
曾经漂泊的心也因与父亲的畅谈而安定,桌上常温的水,书本精致的皮套,盒子里稚嫩的儿童影碟,发霉泛旧的巧克力糖纸,都有父亲的温度。
爱从没有缺席,只是我从未真正到场。
其实所有的不快都是快乐,一个人的达观不是迷信得求神拜佛所能得,而是自我的常省,自我的修复。现在的我感谢曾经制造深渊的自己,更加感谢走过深渊的那个全新的自己。
巴菲特说过“我见过蚕蜕皮的样子,我以为那是会疼的。而现在,我将孤独的一面翻转,将胸膛向世界敞开,我就知道自己错了,原来蜕变是种温暖的自由。当有人逼迫你去突破自己,你要感恩他。他是你生命中的贵人,也许你会因此而改变和蜕变。当没有人逼迫你,请自己逼迫自己,因为真正的改变是自己想改变。蜕变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每一次的蜕变都会有成长的惊喜。”
明白生活的意义,从幼年到壮年到老至死,都欢欢喜喜地过去,一步一步,多是超越苦难的新人。
一路长歌,且大胆地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