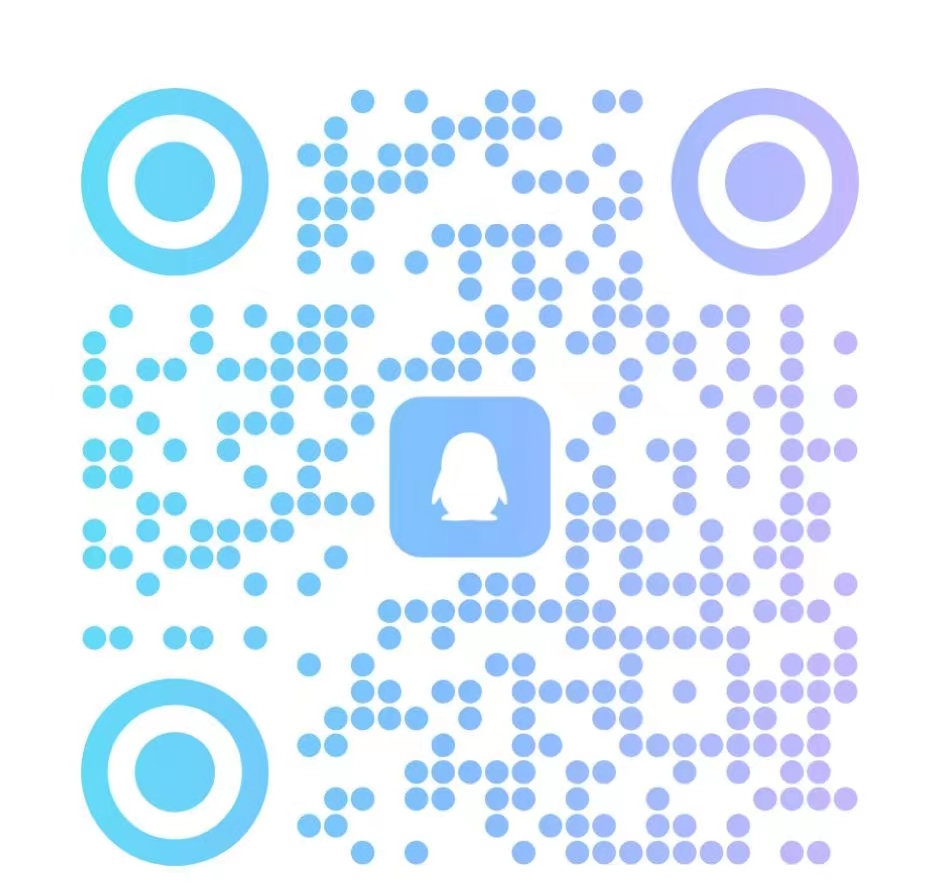如果一只膏黄饱满的大闸蟹在被葱姜环绕的锅里蒸上一个小时后没有被我吃掉,我都不敢想象它会有多难过。
淄博这两天下雪了,簌簌的雪粒子就跟神仙扬麦子一样从天上劈头盖脸地倒下来,一会儿地上就堆起厚厚的积雪,人踩在上面便咯吱咯吱地响。
都说下雪了南方人比雪好玩,我却没那么兴奋。雪,我们那儿也是常有的,虽然不像这里的干,堆得不如这里的快。
不光是雪,很多其他的东西——例如植物和建筑——两边都是有的,不过不太一样罢了。所以一直以来我都不怎么想家。
如果说,现在的我看着雪觉得很冷很难过,那大概也不是我想家了,而是家里的大闸蟹想我了。
大闸蟹和羊汤都是家里冬天必备的,家住金坛,临近长荡湖——出于盲目且不可相信的主观判断——那里有最好吃的大闸蟹。俗话说九雌十雄,古人讲究“九月团脐十月尖,持蟹饮酒菊花天”的意境,对我而言,晚上坐在桌边讨食小狗一般摇头晃脑等着妈妈从厨房端出最后压轴的一盘大闸蟹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在家里,仗着父母惯我,我只吃母蟹。先撬开壳,将嫩红鲜黄的蟹黄一扫而尽,我以小人之“腹”揣测这大概是每个吃螃蟹的人最开心的时候。温热的蟹黄没有一点腥味,也不像鱼籽那样有明显的颗粒感,大部分成块状,小部分成浆状,都鲜美异常。蟹螯吃起来要比蟹脚麻烦得多,而且母蟹蟹鳌肉少,我总是懒得去弄。蟹肉洁白似玉,味淡而鲜,一般人家吃蟹总要沾姜醋即一碟醋泡姜丝,我也吃不惯,于是吃起蟹来毫无仪表可言,连筷子也不用,直接上手。所以有的时候想想老祖宗那些蟹八件之类优雅的物件,也会油然而生一丝羞愧。
今年大闸蟹上桌的时候我远在淄博,其实如果好好清算一番,我还错过了腊八粥——大排骨被炖得化在粥里,配上青菜,豆腐干和芋头,微咸,放到稍温的状态,我可以连喝两三碗;外婆家自己灌的香肠;这里也没有妈妈做的土豆丝,可乐鸡翅和素鸡烧肉。
食物是思乡的前哨站,一个地方再怎么与故乡相似,哪怕从气候到建筑都克隆了去,也学不来故乡食物哪怕半分的韵味。
我在淄博纷纷扬扬的雪里,塞满煎饼和馒头的胃毫无征兆地思念起了大闸蟹的香味。
香味从故乡而来,从江苏常州一个小小的城市而来,它从那搭乘高铁要坐上四个多小时,经历十几度的温差才能到达这里。
它大概会难过,它大概会想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