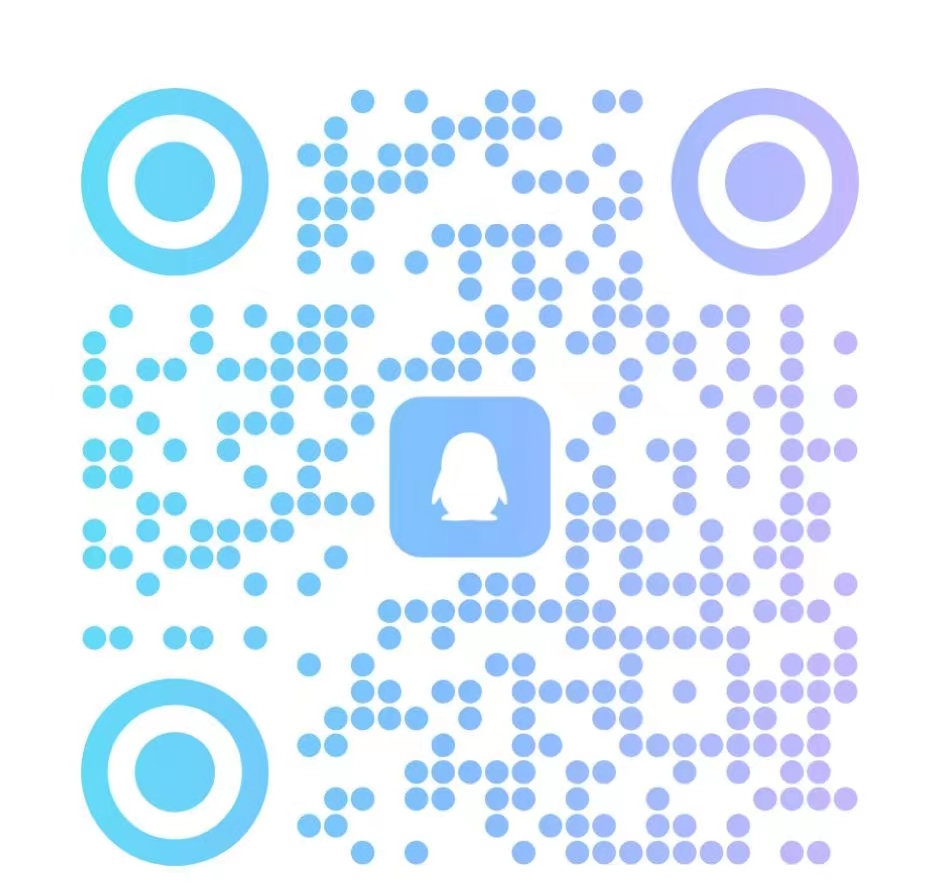如果有人在你最容易被辜负的时光里陪你走过那么一段,那么她一定不会在你波涛深邃的内心世界里倏忽而过。梦想这东西太过于冷暖自知,太多时候你独自走在生命的钢索上,所以才更加知道老师是多么重要,你希望和他的人行道交织在一起,可是迟早,故事都会有个结局。
每周去医院探望她,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十二岁那年,我第一次见到她,从座位上看向讲桌,一个高高瘦瘦的女教师,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可以想象,刚刚成为我们老师的她心里有怎样的起伏。铃声一响,走廊里总是人影错杂,但是在那么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她的位置,一席短发遮不住她已泛黄的脸庞,佝偻的背影诉说着她疲惫的曾经。她总是带病给我们上课。她的心脏病是几年前得上的。“年轻时总是与人动肝火,后来岁数大了,心气渐渐跟不上了。”每当问起她的病,她总是说句:“谁脱下衣服没几个伤疤。”
十二月初,校园里的枫叶都被无情的冷风吹的沉沉下坠,落进厚实的积雪,结成冰,树叶便与这片土地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即便是推土机,也难以撼动树叶与其深厚的乡情。这片“滑冰场”的打扫工作便落在了我们班头上。那天早上,风凛冽的尤其厉害。她扛着铁锨,一块一块的把冰面击碎,然后铲进垃圾桶里,一边打扫,她还时不时抱怨道学校怎么想的,让学生干这种活之类的话,近景看去,她的手冻得好似正握着一柄烙铁,那种红,不像枫叶的红。可是冷风并不像是要施舍那么一点怜悯,窗外,操场,风肆意吼着。那阵我们过得似乎特别轻松,不用值日,要抄的板书也少了,大家以为老师终于放弃了灌输给我们那些无用的原理,但事实——她的手拿不起粉笔了。
我十五岁那年,她被调往台湾做交换导师。有时候生活让你真正的颠沛流离,也是无可奈何的。每个周四她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她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待护照检验;有次我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她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我一直在等候,等候她消失前的回头一瞥,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次也没有。
长时间生活在这种两地奔波的路途中,正常人的身体也早已累垮。她住院了。同学们一起去看她,我们把鼓励都放进相片里,把她的话变成最动人的音符,把我们大家最深最动人的曾经永远延续。我开始每周去看她,但是她依然要赶回台北,每周四她拎起皮包,我接过她的轮椅,看着她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爱难忘冗长。
我慢慢的了解到,所谓师生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她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地在目送她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她逐渐消失在小路的转弯,她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而我,只能在玻璃门后默默祝福你,愿世界不再许你颠沛流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