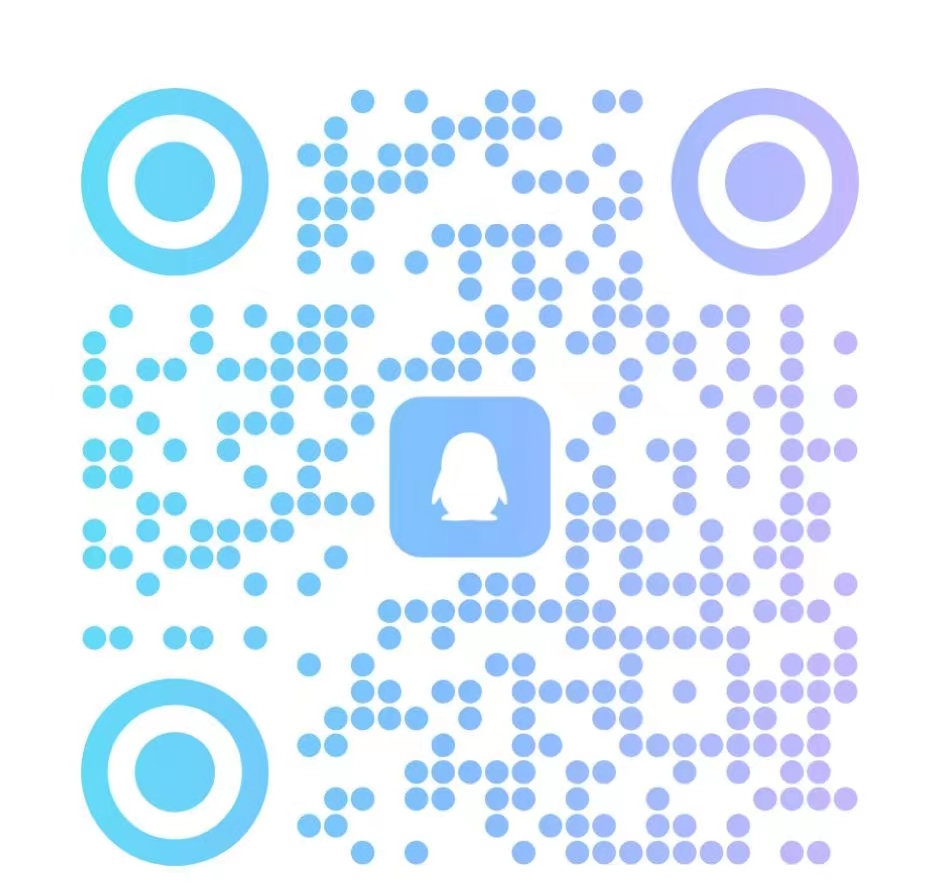凌晨四点半,静谧的房屋里,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仿佛有无数双陌生的眼睛在黑暗的秘影里盯着我,陌生、新奇。噩梦将我从睡梦里拖离出来,乘着床前明月光,依稀看清眼前的模样,这是来到这个陌生城市第二天。
呼和浩特乘火车到学校近十八个小时,从踏上火车的那一刻,我背离了家乡,也没曾想过,再回去的那一天是否还能看到家里的春秋。火车爬上小土丘般的高处,钻出松林,秋日的阳光从树梢间洒下,留我一个人在火车上目光似游离般呆坐着,我想,我这次真的是一个人了。

有人说,大学是几万人在一个城市孤独的生活的地方。来到大学,似乎一个人的生活确着合乎情理,在大学里看到了太多一个人的自习,一个人的食堂,一个人的路途。现在还记得开学的前三天,宿舍里六张床铺来了四个人,第一天我们沉默的看着手机度过了。第二天,我们还是看着手机沉默的度过了。到了第三天,我再也忍不了,问道他们,从哪来,“东营”,你呢“枣庄”还有你“滨州”,“哦”,于是我们沉闷的度过了第三天。
就像俞敏洪从他舍友身上学到的“嘲讽文化,批判精神”,我也从我这天赋异禀的五位舍友身上获取了很多。小玉虽是北方的汉子,我却看到了江南女性的细腻,做事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我常诧异他是如何从几百人里脱颖而出进入资管委,能够从容的每周在大学生事务中心值班六次,还能按时完成作业,名次班级前三,怀疑这小子是从哪得到高人的指点,还是吃过一些所谓开过光的灵丹妙药。子明是个典型的山东人,为人实在是给我最大的体会,现在我还记得班里投票选裁判,全班30人,他29票,因为他自己的一票投给了别人。他也是个奇怪的人,也正因为这个奇特,让我更钦佩,无论课程多么紧张,他总会按时九点回到宿舍,坐到书桌前翻开练字贴,这便坚持了一年,虽然我也没觉得他的字有什么长进。他总会按时十一点熄灯上床睡觉,床侧的墙上贴着一幅中国地图还有“无极”俩个大字。刘天成,这是我第一次叫他名字,我们宿舍统统叫他好人,以至于他走在大街上,别人喊一句“好人”他要盯着人家半天,探探究竟。好人是名副其实的学霸,一天里大概只有中午还有晚上能看到他,他太优秀,太认真。我可以把所有的事放心的交给他。看着他帅气而高傲的侧脸才发现,原来男人对男人也是有感觉的。土豪,名为商梓豪。叫他土豪并不是因为他多么财大气粗,更多的是他身上所透露的看破红尘的人世观。我特别佩服的是,他画完一张水粉,我们问道你画的什么,他答到不知道时的豪气。我还特别好奇他是如何频频在课堂梦寻周公,却能在期末考试时华丽转身,我也曾向他看齐,不料华丽转身时脸撞在了墙上,以挂一门高数完美收尾。常青,我相信他是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也是《谁动了我的奶酪》里的哼哼,我从他身上能看到文青的影子,连他睡觉的床铺都有艺术的气息。大学一年里他成功的接受了吉他、架子鼓、单反的熏陶,在新闻网干的风生水起。每天清晨我会准时跟着他5.40分的闹钟起床然后去趟厕所,然后继续睡到七点。我想,我是离不开他了。
有人说,我们的一生会遇到八百二十六万三千五百六十三人,会打招呼的是三万九千七百七十八人,会和三千六百一十九人熟悉,会和两百七十五人亲近。我很庆幸他们就在我那二百七十五个人中。他们朴实,淡薄,他们不会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一些无关痛痒的安慰,相反,他们会带我喝的酩酊大醉,给我的思维另辟蹊径;他们不会陪我一块在雨中淋雨,而是会及时的递上一把伞;他们不会和我每天厮混在一起,但是当我们某个下午交谈的时候,我总会豁然开朗。

我害怕,我害怕未来的某一天再回到我们的家,我再也看不到热热闹闹的你们,再看不到我们曾经嘻喧欢笑的场面。我害怕床上再也没有文青的气息,墙上也只剩一抹苍白。我害怕房间干净的如同太平间,窗玻璃光可鉴人。
我害怕,我害怕离开你们,给与我关怀,给与我爱的你们。致我的室友,致我一辈子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