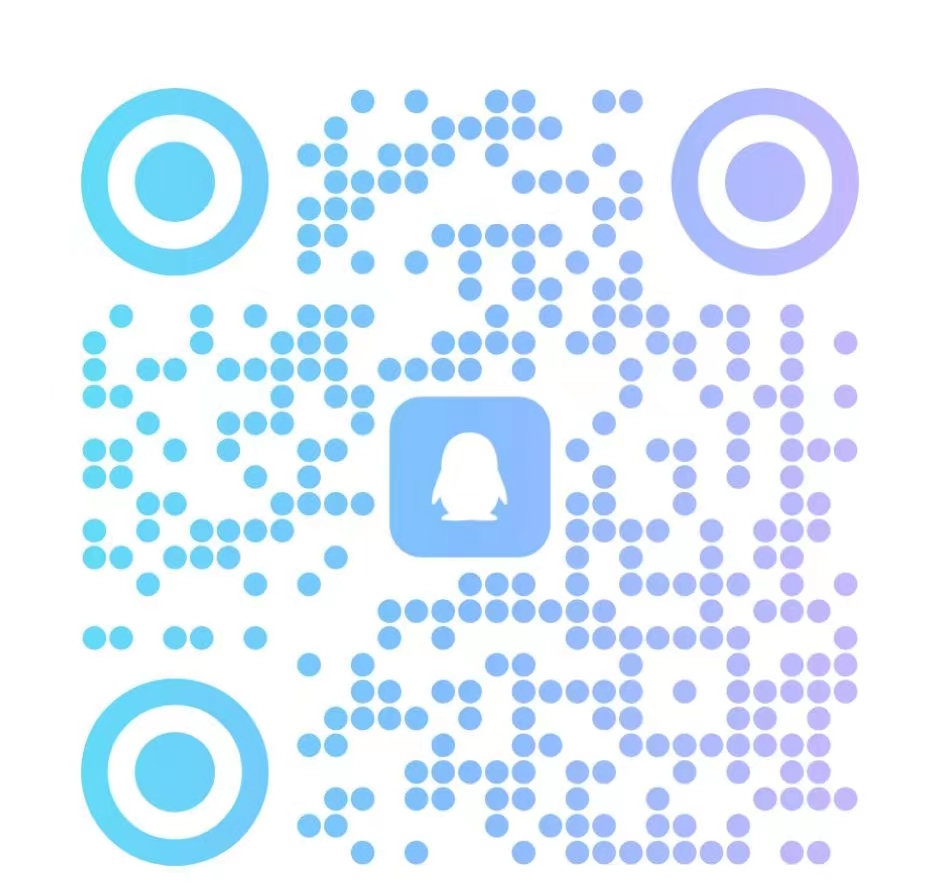十月的风,褪去梢头枝叶的青涩,将枝干微微晃动,每一次摇曳,都会缓缓坠下几片零落。天气还不算凉,可舅舅却提前披上了厚重的外套,他说今年的风吹得挺冷,一边说着,一边拉紧了衣袖。也是,六十多岁的年纪,不再像曾经那么生猛,早已磨灭了当年打拼的劲儿头,岁月悄悄爬上了舅舅的鬓角。
舅舅老了,但在外婆面前却还想孩子一样,两人常会因为小事而拌嘴,外婆气得总要向我们告状,说舅舅哪里做的不对,母亲夹在中间,怎么也说不出谁对谁错,但总少不了一句“哥,别老和咱娘吵”。外婆只是瞪着眼睛瞅着舅舅,随后拄着舅舅给她打好的拐杖去做饭,母亲想要帮忙,却被赶出来,八十多岁的外婆,还是这么倔。父亲等他们说完,才去陪舅舅聊天,而我,则喜欢听外婆讲舅舅年轻时的故事,外婆记得一清二楚。舅舅早已是当爷爷的人,但他却一直跟着外婆吃饭,我不理解,为什么外婆八十多岁还不肯歇着呢?但外婆说:“打小就跟着我吃,我不做饭,他吃什么?”
十月的风吹熟了麦田,吹来了丰收。以前家里的农活舅舅都要亲自去做,不管别人如何劝告,他都像外婆一样倔,怎么也听不进去,好像农活少了他不可。但今年,舅舅没再做农活。
上车前,外婆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唠叨不停:“不让他乱吃东西,非不听,这下住院了,这么大年纪高血压一时半会可好不了。”舅舅住进了医院,母亲把外婆接到家中,外婆不用再做饭了。下了车,外婆指着家门前的石榴树说:“这树今年结了不少果吧。”母亲搀着外婆说:“多着呢。”石榴树是舅舅前年在我家栽下的,外婆还是记得那样清楚。
十月的风,仿佛不曾断过,一阵又一阵,拉扯着快要落光的石榴树。谁也没想到一切来得会这么快,舅舅坚持要出院回家,但不肯告诉外婆。电话那头,外婆还高兴地说,舅舅的病快好了,不要让我担心。可我心里却不是滋味,电话才挂断,就接到了短信,舅舅走了,癌症晚期,虽然有过准备,但还是太突然,更可惜的是,舅舅没有见到外婆。
十月的风,吹得确实太冷,外婆说想回家去,等舅舅回来好为他做饭。母亲几欲不忍,都被父亲拽住,说再等些时候。外婆又坐回门前,只静静地望着风中摇曳的石榴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