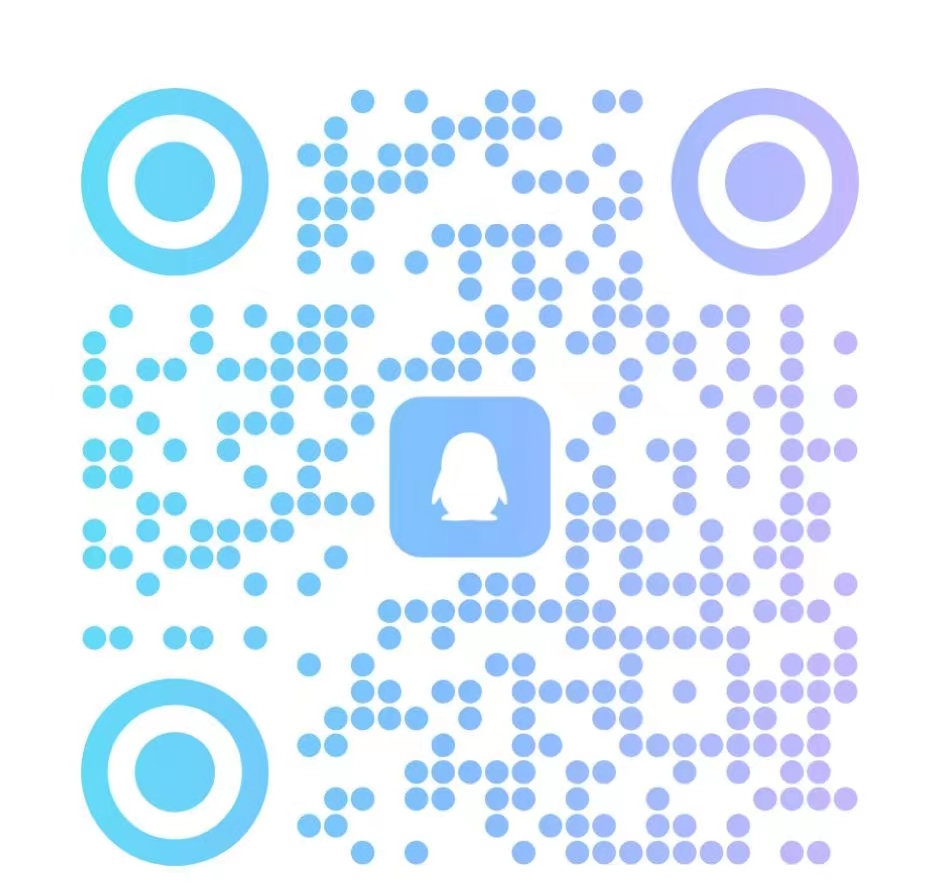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迷失了方向,曾经的热血逐梦少年,现在开始变得麻木,世俗。隐隐约约,混混沌沌间还曾记得自己许下的“不执子之手,亦与子偕行“的诺言,少年的狂妄和不羁,在二十岁的自己眼里成为笑谈,但又有一种或许,少年时的自己对已及尽弱冠永远带着一副伪面具的现在的我也有一种想竖起小拇指的嗤之以鼻吧!!!
——题记
当我们喜欢拿“长大了“来搪塞自己,或许我们已经走进了另一种禁锢。我们变得不再喜欢冒险,习惯着用教条和规矩来”规范“自己,开始用懒惰和蜷缩在被窝来表明我们对这个世界各种不满的抗争;说话开始小心谨慎甚至唯唯诺诺,最后变得言不由衷,我们还调侃的自夸自己八面玲珑;有一天梦想变成了一种奢侈的东西,我们甚至忌讳谈论它,偶尔有那么一个不识时务的家伙高调的叫嚣他的理想,我们肯定会送给他一个鄙夷的眼神作为对他梦想的“支持”,因为在我们这群“聪明人”眼里他们诠释着一个词——好高骛远。
我们讨厌一个学科或在一门课程里取得少的可怜的分数的时候,我们仍然会理直气壮的给自己给父母给周围的任何一个人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我没有兴趣。即使这样我们也不愿承认自己懒,我们会大声的叫嚣——如果我想做,谁都比不上我,可是我不愿意做。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两袖清风,准确的说我们喜欢标榜自己两袖清风,把懦弱和胆怯当做一种对生活的淡然,我们害怕挑战,甚至不愿意动脑子,所有得不到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不喜欢争!当有一天,我们的偶像都变成了陶潜,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成一种修为;当有一天,我们的话语变得厌世﹑激进,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只剩下各种不公平,眼里折射出太多对“二代”们的愤恨,但又一边抱怨为什么自己就没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爹;当有一天,我们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永远抱着那不是为我准备的,里面肯定有猫腻的想法。在这种时候,我们会不会问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曾经的梦想是什么?

我是谁?
多么弱智的一个问题!!!我是我呀,我有自己的姓名﹑年龄和代表着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号码。是呀,多简单的回答——我是我呀!这个回答永远是那么美好。“我”不再是一串求职者名单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名字,“我”不再是每年700万大学毕业生档案中薄薄的一页,“我”不再是这个城市成百上千万忙碌人群中一个籍籍无名的小角色。我是我自己的主宰,是我父母家人的希望,是爱我的人的全部和唯一,和我爱的人的依靠和支撑。我们总是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对这个现实的世界是那么的无力,我们似乎永远是被要求﹑被剥削,可是我们忘了,有那么一些人,我们就是他们的全部。
我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我在上大学呀,我是一名大学生,我们一定很干脆的回答。或许十年前,这是一种充满着多少无限遐想的生活,那时的我们感觉大学就是伊甸园,是自由和生命活力的象征,在所有人的口中,把它形容成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终于有一天,我们和自己的大学生活“邂逅”,发现它没有那么美好,它是那么的“懒惰”和“矫情”。总算明白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它为什么美好,因为可以没有压力,可以肆无忌惮的挥霍,甚至可以不负责任。但在另一些人眼里可能还存在另外一种美好吧,这种美好叫做充实纯真和希冀。
我的梦想是什么?
如果五年前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会给你很多答案,这些答案可能天马行空也可能真挚务实,但最主要的梦想一定是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但现在,作为一个大学生的我,你再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会感觉这个问题有点“奢侈”,“奢侈”的无从回答。后高考时代的我们,缺的就是“梦想”,因为事实让我们来不及考虑这个问题,为了“面包”,为了生计,我们跟着大部队“奔波”就可以。我们总是习惯说看不到未来,仔细想想,谁又能看到未来那。有一个梦想,我们凭着记忆对梦想大概的“轮廓”勾勒,或许能创造一个“梦”一样的现实吧。
有一天在一个寂静的巷道了,天很黑,偶有微风吹过,我打着伞前行。前面行走的人忽然停下,是一少年,少年转过头,我看到了少年的脸庞,那是十四岁的我,他在对我微笑,似乎在赞许现在的我带着当初的梦过的很好,我亦知足,因为我依然义无反顾的走着寻梦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