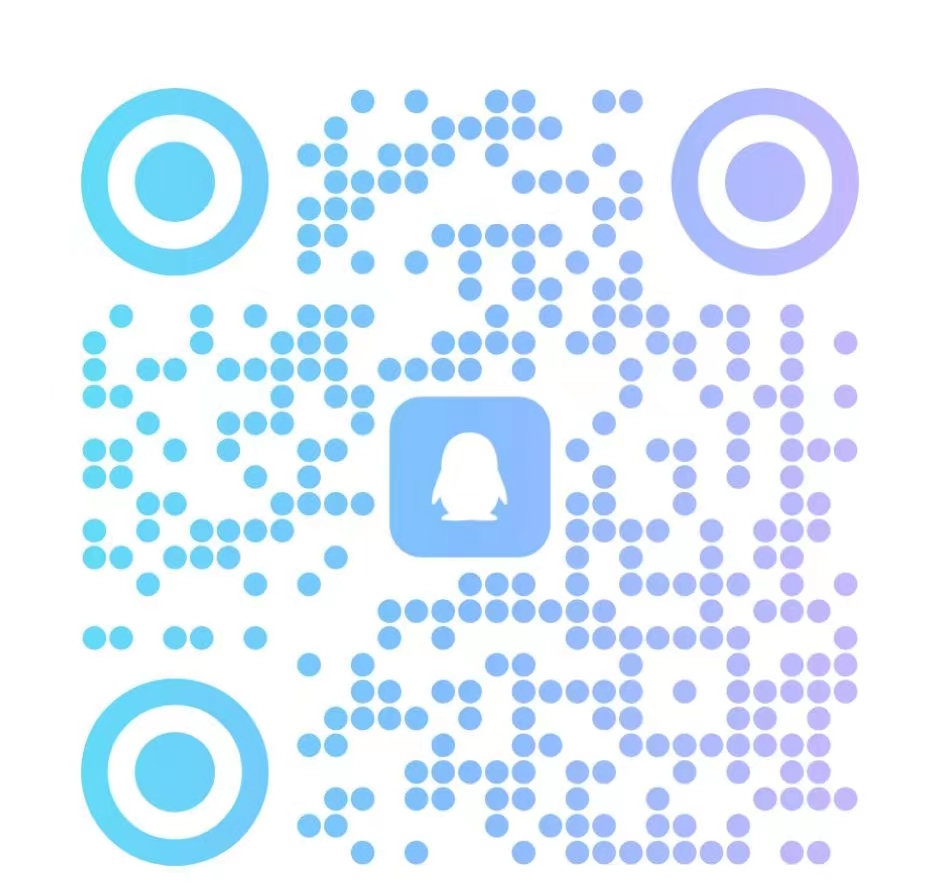一个在上海打寒假工的朋友在得知自己挂科后,满腔愠火地给我发来一条消息说再挂科就要跟着我姓。他的悲愤跨越几千公里传播过来,我却纹丝未动地想着其他事,并不是在想怎么慰藉他,而是澄清名字和自身的关系。把自己的姓作砝码它还压不起一个鸡蛋,不管中国人将它看得多重,事实就摆在眼前,它只能是精神领域的重物,因为中国人都喜欢把姓氏和祖宗联系起来,分量似乎就重了。
首先我们的意识观念像多米诺骨牌容易被击倒,传递,从祖宗到现代,一个姓氏在晦暗中延续,为了维护它,一些家庭卯足劲生男孩,一胎是女孩再试第二胎,第二胎是女孩再试第三胎……而很多妇女似乎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个观念。生孩子是不容易的事,一个观念却能让人承担起这样的压力。
日本人在学习唐朝礼制前是没有姓氏的,而犹太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往往用古代英雄的名字作自己的名字以示崇敬。由此看来无论是姓氏还是名字都不会使历史欠缺,一个姓氏的延续并不能证明一群人死了还像活着一样,放下了它负担会减轻很多。

名字是一个称呼,一个名词,它能使人卑微也能使人骄傲。在娱乐圈,很多明星包装了自己的名字,刘福荣变成了刘德华,邓诗颖变成了邓紫棋。名字能给人带来功利,即使它并不如想象中得人所愿。没有多少人愿意看到一个人的名字比实力更重要,尤其是在职场,名字造成的片面的判断甚至剥夺求职者施展才华的机会。好在在文学的国界里真正有一些能放下名字和功利的人,拿着一个如草芥的笔名写下煌若星辰的文字。
谈到文学和名字这两个词,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一个人物。他的原名叫杨百顺,一生中至始至终最敬佩的一个人是替别人喊丧的罗长礼,为了听罗长礼的喊丧,他逃私塾甚至放下手上的一切事情。作者写他对罗长礼的痴迷很巧妙,提前给小说的前半部分一个答案。杨百顺没有因为他的名字讨得吉利,百事不顺,后来遇到住在延津县城到各个村庄宣扬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老詹,做了他的徒弟改名杨摩西,原因不是他想信上帝,而是没有出路。后来他入赘跟着死了丈夫的吴香香过日子,被迫改名吴摩西,再后来他带着巧玲(吴香香和前丈夫姜虎的孩子)去找跟着银匠铺的老高私奔的吴香香,结果在新乡东关的鸡毛店巧玲被初次做人贩子的老尤拐走,悲愤交加的他向着宝鸡一路西去,改名罗长礼。
经历了生活的重重坎坷,他三次改了自己的名字。小说揭示了人处在命运当中的渺小和悲剧性。相比于明星为了争取名利改名字,这类人仅仅为了活着改名字更体现了它的微不足道。活着是一个没有文字和符号的命题,怎么活和为什么活这样的问题一旦击中人,头上便有一片阴翳铺展。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着,没有勇气割断一些与现实的羁绊,名字或许只是这根粗绳子当中的纤弱一丝。
布鲁诺•舒尔茨正是与生存斗争的作为写作者的剽凛骑士,与卡夫卡相似,体弱多病,在工作和家庭关系中步履维艰。他保持着一个抗争的世界,并用《鸟》、《蟑螂》等一系列异化“父亲”的作品柄恪如一地刻了一个父亲形象,执着了地表明了他不妥协的态度。在《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中,舒尔茨笔下的“父亲”变成一只螃蟹被母亲煮熟,母亲将他煮熟的原因被隐藏。家里人围住餐桌却无法举起叉子下手。作为螃蟹的“父亲”最后翻出盆子,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朝着没有家的方向逃走,一路上断腿不断地脱落在路上。
当我需要作出割断某些羁绊的选择并且有足够的勇气的时候,我也会做一只煮熟的螃蟹,让一路上的断腿肥沃土地。同时我会放下名字,不因急功近利而让它锋芒毕露,也不因陈规旧制让它接受刑罚,转而让它拉近与人的距离。当几个学弟学妹不再称呼学长转而叫我名字的时候,我的心情和屌丝逆袭了女神一样愉悦。